向往澜沧江源
直到此时,我才忽然想起要照相。然而,等到我从层层设防的摄影包里取出并准备好照相机,浓雾已将山顶尽皆笼罩,阳光业已隐去,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及至到了山口,我请司机李师傅停车,妄想站在高处找回刚才的景色和感觉。虽然也阳光渐露、群山隐现、云雾依旧,但是刚才的壮景丽色和心中感觉已全然不复存在,山口处的星象山亦缺少了山下视觉中雄伟壮观的气势。可见此时此地的我已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了。匆匆照了几张照片,便上车下山。
以星象山为界,阳坡成为该县唯一的常绿乔木树种——大果圆柏林分布的西北部界线,而北坡则分布着青藏高原特有的山生柳高寒灌丛。下了山,很快就到了扎青乡。
“扎青”是藏语,意思是“高大的岩石山”。海拔4 230米的扎青乡所在地是扎曲的一条重要的支流——布当曲的河谷盆地。方圆不到10公里的河谷地带在群山环抱中就象一片小平原一样显得格外宽阔、平坦,清澈见底的布当曲河水蜿蜒着绕过乡政府而从平原中间静静地流过。如此坦阔的河谷盆地在这峻岭重重的布当曲流域是不多见的。若是修建一座水电站,把这里作为水库,倒是一个理想的所在,而且库容量也会很大。
扎清乡政府的大院内包括办公室和住宅在内,只有几排简陋的房屋,七八只野狗在长满乱草的院子里游荡。旁边有一所乡办的寄宿学校和一家小商店,周围还有几家牧民的定居点房屋,再远处可见几户炊烟袅袅升起的黑色牛毛帐篷和星星点点的牛羊。由于乡里的干部大都在个牧业点检查工作,所以这里显得有些冷清。这种场景是所有高原牧区的乡政府所共有的。上午10时40分,我们的车队停在乡政府的院子里,只是匆匆装卸了一些物品,顺便给留乡干部和学校的校长打了个招呼便又急着向前赶路了。
离开扎青乡政府,走过布当曲大桥,我们的车队朝着更高海拔的高原面上驶去。
这一带的植被显然已与前面的有所不同了。在海拔4 450米的高原面上的山地阳坡地带,由于海拔的逐渐升高和地形、地貌的变化,以及整体水热条件和强风的影响,典型的高寒草甸植被的分布面积正逐渐缩小,并且隐向局部地段,代之而来的是在相对较陡的阳坡沙砾质地段出现的非根茎性繁殖的杂类草草甸。其中的优势植物分别常有密花翠雀、高山唐松草、独一味、高原荨麻、摩岭草、微孔草、筋骨草、大花蒿、红景天等。这类植被不但不能形成致密的草皮层,所以保持水土和改造土壤的能力很差,而且很少优良牧草,对牧业生产不利。因而这一带是扎青乡草场质量最差的牧业社和牧业经济发展最滞后的地区。
我们的车队又有3辆车先后4次出了故障,都是轮胎爆裂,正在一前一后地抓紧抢修、更换。虽说通往高原乡村的路况不好,很差,甚至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但是在半天之内连爆5条轮胎的车队恐怕也没有什么好车。一直走在前面带路的孟书记的车,今天已经是第二次爆胎了,已无备胎可换,只好在荒野里焦急地等待着后面的车。谁知后面的相同型号的两辆北京吉普车也都在更换轮胎,所以,等来的仍然是无可奈何。好在我们的另一名向导——乡武装干事扎尼,从住在附近的岳父家拦截了一辆前来拉牛粪的车并借到了一条轮胎,总算是4辆车又都能上路了。
一天下来,我们车队行车的时速是每小时10公里。
傍晚时分,我们4辆车相继来到了扎青乡格色村一片海拔4 600米的草地。这里驻扎着青海省地质队的几顶帐篷。对于我们的到来,地质队员们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当晚,我们就扎营在这里。一方面是为了了解进入源区的路况,另一方面也为了不辜负地质队的盛情挽留,起码我们不用自己埋锅造饭。
考察队初次在野外宿营,多数人对野外扎营都不熟悉,费了好大工夫,总算绳套绳、帐莲帐、拥拥挤挤地扎起了帐篷,又把所有的汽车都围在帐篷的周围,生怕夜风吹来,人被冻坏。夜晚的天气能有多冷,我虽暂时不得而知,但从大家怨天尤人的谈话中,我已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支队伍畏冷的心理已无法温暖过来了。
果不其然,当我们围坐在地质队帐篷中燃着熊熊大火的火炉旁,吃着地质队员们专为我们做的饭菜的时候,有人已经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这荒山野岭的,哪有汽车走的路,能不能不去冰川了?”“当初是谁主张要去冰川的?靠我们这几辆车能走到源头吗?干脆在附近凑合着拍点儿东西算了。”在我看来,对于许多第一次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参加野外考察的人来说,今天这样的路况和车况以及高山反应带给他们的感觉和影响,使他们产生了担心或者恐惧,也都是在情在理的。更何况小武警尕玛文德已经头疼得不思茶饭了。但是,这时我却发现原先和我们挤在一起,并给我们兴致勃勃地讲述附近路况和自然景观的几位地质队员陆续都悄悄地离开了温暖的帐篷。
两人一顶帐篷,拥挤是在所难免了,虽比一个人躺着暖和许多,再加上鸭绒睡袋上压着一件军大衣,应该不致因冻而睡不好觉。但是,各人平时的起居习惯肯定是无暇顾及了,相互影响自然在所难免,特别是怕打呼噜的人就更难免倍受委屈了,在加上一夜断断续续、时大时小的风雨和各人轻重程度不同的高山反应,所以,大多数人一夜都没有休息好。
9月6日,为了拍摄照片和做植被样方,我和许国海起了个大早,等待日出。及待其他人起来,我们已各自收获不小。起床后的所有人都没有心思做饭,仍然去吃地质队的大锅饭。
早餐后,我们抽出部分人分乘两辆车继续向源区的冰川进发。一路上,扎尼和孟书记都说应该4辆车一起走,并说我们昨晚的情绪已经影响到他们原有的热情了。说归说,但是他们仍然表示愿意尽力帮我们走向澜沧江源区。
车子在高原上时有时无的所谓“路”迹上艰难地前进着,时而费力地爬山,时而小心地过河。车里的人也随着车身的摇晃和颠簸摆动着身体,更随着“路况”的不同而变换着心情。我虽不能例外,但却也从未忘记自己的专业考察。每当这时,就是我抓紧记录和拍摄沿途景观和生物多样性现状的好时候。虽然车身的摇晃和颠簸常使我的记录歪歪扭扭,甚至自己写的字自己常都不易认出,句子也常前言不搭后语,但我还是一有机会就不停地写。因为,作为野外考察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记录对于我的专业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对于高原的自然景观和众多的高寒植被类型,我也会抓住机会多拍一些照片和幻灯片。这类抢拍的照片虽说不能与摄影家架机、候时、等光的摄影作品相媲美,但是,作为真实、难得的科学记录和科研、科普资料,无疑是十分珍贵和必不可少的,何况我多是以千分之一以上的快门速度进行拍摄。而对于许多必须在静止状态下拍摄的高原特有的动、植物的自然形态及其生境,我则常常是以不同角度的特写形式来表现的。
两辆车子小心翼翼地先后驶过了一条流量不算太大的被叫作托吉曲的冰川河,在对岸的河滩里停了下来。这里已经是扎青乡红色村的地界了,距离在上游被称为扎曲的澜沧江源区河流的发源冰川已经越来越近。这是一条从源区海拔5 876米的色的日冰川主峰源出的河流,沿着这条汇成扎曲的数条之一的源头区一级支流,溯流而上就可以到达冰川脚下,观揽江源。
这里的河滩宽阔而平坦,托吉曲在河滩中间蜿蜒流过。河两边沙洲片片,除了生长着少量稀疏、低矮的耐寒灌木——水柏枝以外,更多的却是大片大片的西藏沙棘灌丛。西藏沙棘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耐寒耐旱的高原、高山矮小灌木,还是高原面上难得见到的少数几种灌丛之一,而且是青藏高原的特有植物。其分布于青海、西藏、甘肃和四川西部,常生于海拔3 300-5 200米的高山石隙、沙砾河滩、河谷阶地等处。沙棘属植物的果实味道酸甜可食并含有丰富的多种维生素和有机酸等,是制造“三刺饮料”的原料之一,还可酿酒和制果酱;其种子除可榨油外还可与干燥果实同样入药,有补肺、活血的功效,可用于治疗月经不调、肺结核和胃溃疡等症,是藏医药中的常用中品;树皮含鞣质,可提制栲胶;这类植物还是防风、治沙及保持水土的良好种类。西藏沙棘虽然只有15厘米左右高低,但是它的果实却是所有沙棘属植物中最大的,它的利用价值也应是非常之大的。还有,它作为难得的茂密高寒灌丛分布于本区,对于地质年代轻、土壤成熟度差、植被稀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澜沧江源区的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作用亦应该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西藏沙棘这种独特的生态资源本身首先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我们在这里考察时见到了成百上千只红嘴山鸦组成的长阵飞起飞落于西藏沙棘灌丛中采食其果实,它们对于西藏沙棘种子的传播及其分布区的扩大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除了西藏沙棘灌丛,这一带还有大面积成片生长的独一味、摩岭草、大叶龙胆、红景天、密花翠雀等高原、高山特有的药用植物,使本区的药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在合理开发、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是使本区摆脱单一牧业经济、迈向小康的出路之一。
沿着托吉曲,我们的车溯源向色的日冰川方象驶去。途中偶尔也可见几户当地牧人的帐篷和不多的牛羊。而最在意我们到来的还是路边帐篷中牧人所养的藏狗,只要听见或是看见我们的汽车,它们就会冲着我们吠叫,或是远远地追上汽车狂吠乱咬。在一片坦荡的河边草地上,我们发现一只细瘦的黄狗正在撕扯一只被咬死的小羊。看见我们的汽车,那狗跑开了,但却并未跑远,而是在河对岸远远地望着这里,舍不得离去。我们都说要是有枪的话应该把这只偷羊的狗打死,但扎尼却说这里的牧民是不会这样干的,并指着远处走来的两个人说,他们就是羊的主人,是来抓这条野狗的。我们看着他们在有死羊的地方挖坑埋下了铁夹子,做好了伪装,再把羊肠子堆在旁边,然后背起死羊转回了帐篷。我们也离开这里继续赶路。
色的日冰川距我们越来越近,皑皑的雪峰已清晰可见。我设想着走进源区冰川的情形并不时打开随身的两架照相机,随时捕捉可供拍摄的景物。
在河边一处石灰岩露头的台地上,我们停了车。在这台地下边有一片据说能够治疗多种疾病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温泉,常有远近地区的群众为治病而结伴前来泡温泉澡。今天,就有几个远道而来的当地人正在洗浴驱病。温泉的面积约有百余平方米,从河边的岩石下或河滩砾石层中等多处不断冒出滚烫的热水。石崖下有一处约60厘米深的水池,同时开着一个出水口和两个进水口。一个流淌的是来自温泉的热水,另一个引来的是河沟的冷水,倒是便于调节池中的水温。除了拍摄工作以外,我们也都坐下洗脚,据说近期正被胃病困绕的扎尼径自下到水中泡澡治病。这里由于较高的水温形成了较温暖的小气候,所以,在周围植被一片枯黄的大背景下,河边石崖下生长着的高原荨麻等植物却还正自郁郁葱葱,非常茂盛。这种温泉在青藏高原上是并不少见的,并且许多温泉都被用于治病。
除了高原荨麻,在这里分布较多的还有一种叫做大叶秦艽,能入药治病的植物,正开着淡黄色的花,花间不时有昆虫飞来采蜜并为之传粉。最常见的是熊蜂,它是高原地区较大的一种昆虫,许多高原植物都需要它来传粉,据说在其营巢的地穴里常可挖出蜂蜜来。我们虽无此雅兴,但我却把它们在大叶秦艽的花上采蜜传粉的情景拍了下来。
由于在这里耽误了较长的时间,又加上据说道路难行,以至于我们离开后并没有继续朝着已经清晰可见的江源冰川方向前进,而是相反地走上了返回营地的路。这一走,使我们此次考察失去了走进位于色的日冰川下的澜沧江发源地的唯一最佳机会。
沿着来路,我们又来到野狗咬死小羊的地方。不出所料,那条野狗已经被铁夹牢牢地夹住,无可奈何地躺倒在被用做诱饵的那堆羊肠子旁边,一副可怜相。看见我们过来,原本躺卧着的野狗哀鸣着,几次都想挣扎着站起来,但却由于铁夹的牵绊和伤痛而都失败了。野狗那条被夹住的左前腿的骨头已经断了,只有皮肉还连着,并有血液渗出。看到这里,大家早已忘记了不久前才惨死的小羊,反倒都觉得这条狗挺可怜的。
布设铁夹的人来了。他们用一件破衣服缠包住狗头,再用绳子把狗的另外三条腿绑住,然后掰开铁夹,解开绳子,放它一瘸一拐地落荒而去。看来羊主人只是想教训一下这只狗而并不想要它的命,这在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江河源区是被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
我们的车在4 490米的托吉曲北岸停了下来,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两个几乎相连在一起的小湖。两个小湖相距约3米远,湛蓝湛蓝的湖水像两面镜子朝向天际,又像是一双“大地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凝望着天空。若从高处向下看去,因水面下降而稍稍陷入地平面以下的两湖水面,各自成椭圆形,则更像是镶嵌在浑黄大地上的一副眼镜,所以,我们都更形象地叫它为“眼镜湖”。眼镜湖的水面映照出蓝天白云的倒影,湖边形成漏斗形的自然斜坡,两湖之间是一道自然形成的高梁,恰是人的鼻梁。因为是在河滩上,所以,坡面上全都是磨圆的砾石。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两湖虽然相连,但却并不相通。作为眼镜湖的两个“镜片”也并不在同一水平面上,而是东边的湖面较之于西边的要高出约10—20厘米。一般认为,冲积形成的河滩砾石地层中的水应是相通的,所以,其水面也应是平衡的。由此可见眼镜湖的两边不仅水面分离,而且水下也并不相通。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位于西边的湖水中生长着茂密的水草,而东边的湖里却无水草。还有,两湖的直径虽然都不足10米,但湖水却都深不见底。我们也曾丢下石块试探水深,水声沉闷而回声迟缓,西边的湖水更是需要10秒以上的时间才可看到气泡上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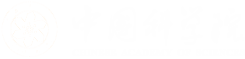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 63010402000197号
青公网安备 63010402000197号